谈及造园,他常从元人倪瓒的《容膝斋图》发端:远山寒林,水面留白,近处一亭四柱,茅顶轻若羽。若把画缘当作围墙,近处亭榭,中央为池,石树相迎,这分明是中国园林的格局缩影。但他更在意的是画题之义:若能在画界内的场景里生活,宁肯让房子小到仅能容膝。此处“容膝”,不是屈缩,而是以小见大,以简得丰。他借此对学生阐明:建造一个世界,不是先造房再配景,而是让房与景在同一价值坐标中彼此生成;在这种坐标里,人居之所不必占据画面的中心,因为在中国文人的建筑学中,总有比房子更要紧的东西,那就是人与自然的互证与和解。他在国内讲此图,常引出价值论的争辩:不先立价值,实践必将迷路;他在美国讲此图,听者则惊讶于一种与所习全异的建筑观。
反差让他更笃定:面对世界的方式,比知识的多少更重要。他把“留白”作为方法论:在平面上留出空场,以容光与风;在立面上减去装点,以显材料的性情;在动线上减少指挥,以鼓励自由的行走。他也强调比例的温良:一根细柱或许比粗梁更能让屋顶显得轻,一段矮墙或许比高墙更能守住亲近。于是,“容膝”变成一种测量:测量人的需要与天地的尺度能否相合,测量欲望能否被节制,测量建筑是否具备把生活放轻的能力。他把这份测量放进每一次设计的起点,让画中那点清寒成为现实世界里的一束清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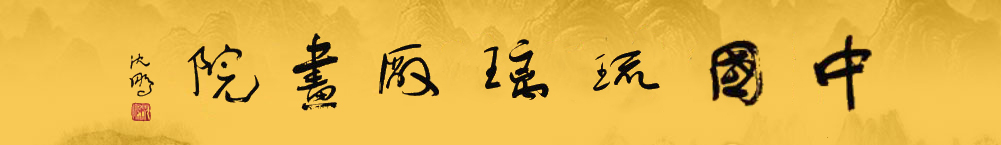

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5723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5723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