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彭郎醉后书更佳。"苏州城的酒肆掌柜总爱这般念叨。每当暮色染透运河,便见彭年抱着酒坛踉跄而来,衣襟上沾着酒痕与墨渍,分不清是醉意还是书意。
他嗜酒,却非文人雅集时的浅酌。要的是市井浊酒,最好是酒坛底那层微浑的老酒。他说:"浊酒入喉,能涤胸中块垒。"醉眼朦胧时提笔,字便活了。有次在寒山寺外醉书《心经》,笔锋如枯藤缠石,墨色浓淡间竟有梵音缭绕。老和尚惊叹:"此经当供于藏经阁,可镇寺百年。"
文徵明不解其嗜酒,彭年笑指庭前老梅:"君不见霜雪欺枝时,梅花愈见精神?"他笔下的拙趣,恰似酒意入喉后的真言。那些看似歪斜的结体,是醉眼看见的人间百态;那些枯笔飞白,是酒意入喉后的世事洞明。
苏州文人圈盛行"以书养性",彭年却偏要"以酒养书"。他说:"酒是液态的诗,墨是固态的酒。"某日暴雨突至,他在沧浪亭醉书《兰亭序》,雨水顺着瓦当滴落宣纸,墨痕随雨势晕染,竟成天然淡墨。文徵明冒雨赶来,见满纸烟云,叹道:"此卷当名《醉墨兰亭》,方不负天雨相济。"
如今站在苏州碑刻博物馆,凝视那方《醉墨兰亭》石刻,恍惚能嗅到千年酒香。石刻上的字痕被岁月磨得温润,却仍能触摸到那份洒脱不羁。就像彭年其人,虽未列"吴门四家",却在书坛留下醉墨淋漓的印记——原来真正的书法,不在法度森严,而在笔墨间流淌的真性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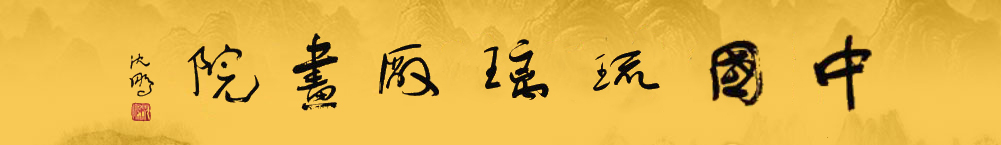

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5723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5723号